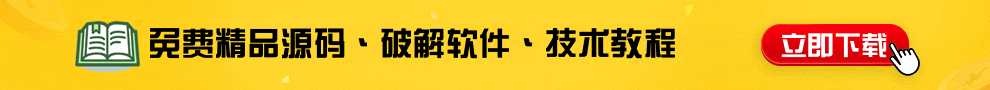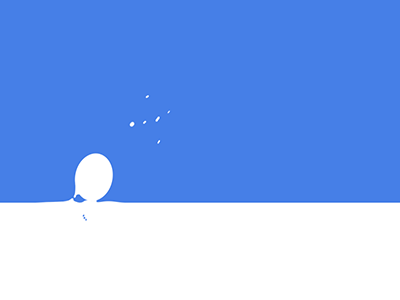铁骑突出刀枪鸣(铁骑读ji还是qi)
立春以来,江南持续淫雨霏霏。难得的放晴日,走进艺术的殿堂,于静心中挥去持续的阴霾,洗涤内心的浮华和喧嚣。
上海博物馆《丹青宝筏——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》展厅内,人潮涌动,众多艺术爱好者驻足欣赏。我伫立在董其昌《秋兴八景图》前,屏气敛息,周遭的人流和嘈杂渐渐散去。
400多年前的旧时光仿佛在画中被凝固,沉入一种宁静而明丽的意境当中。400多年的历史恍如没有留下时光的印记,那些画依然光鲜如昨,散发着迷人的色彩。那个时代的生活痕迹慢慢融化、晕染开来,以某种无以名状的山水风情紧紧地魅惑、包裹着我,把我融入大自然的迤逦风光里,如同穿越到那个时代,行走在明朝的山山水水,驱散连日的绵绵阴雨,一切都豁然开朗起来。
董其昌是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和理论学家,一直倡导“南北宗论”的画风,更推崇“幽深淡远”的“南宗派”。《秋兴八景图》是董其昌66岁泛舟吴门、京口途中所见景色,是其出入宋元的代表之作。有着“南宗派”“率真高古”的禅味,也掺杂了“北宗派”刚性、雄浑的影子。
“八景图”中,既有浅淡的画面上青溪蜿蜒,弥漫着青草绿叶、繁花点点的春意盎然景色,也有红叶层染、万树婆娑、绚丽壮美的深秋美景。而在山林叠翠的留白处,可见云层涌动、变幻无穷的高远意境。更多的是山峦明秀、树幽石奇,于苍秀雅逸、鲜丽而柔中蕴含着独特的韵味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才能获致“丘壑内营”之功,而这正是董其昌等文人集古成家的一条重要途经。
董其昌的字与画一样,到了晚年更加温润、臻熟,达到炉火纯情的境界。他临颜真卿《裴将军诗》,巴掌大的字体,如同万马奔腾,掷地有声,有气贯长虹之势,又不失婉约与温情。近听,有“嘈嘈切切错杂弹、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粗犷。远看,如“银瓶乍破水浆迸、铁骑突出刀枪鸣”的壮观。那一个“舞”字,变势而下的一竖,于千回百转中的婀娜多姿,又雍容又妩媚,真是让人销魂,禁不住“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”起来。
董其昌的行草以“二王”为宗,又得力于米芾、赵孟頫等大家,形成了自己的笔性。
王献之的《鸭头丸》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馆藏镇“宝”,是此次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的重头戏。
《鸭头丸》只有短短的两行15个字,却有方笔、圆笔、侧锋、藏锋等不同的用笔方法。转承起合,疏密有致,连断得恰到好处,一气呵成。现帖卷上钤有宣和诸玺等,文后有“天历之宝”大方印。又有宋高宗赵构赞语,再后为北宋人柳充、杜昱观款,明王肯堂、董其昌,清周寿昌等人题跋,显得更加庄严、神圣。浸润其中,似乎闻到一股从远古飘来的中药味。遥想当年,东晋人注重养生,一群文人雅集时,王献之随性给友人写下的手札,是否想到会成为传世之宝?而“当与君相见”五个字,其迫切与友人相见的心情呼之而出,跃然笔端。就像法国作家波伏瓦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在芝加哥邂逅,短暂六天半的耳鬓厮守,却让两人在异国他乡相互想念,苦苦折磨,渴望着能早日重逢。
一直以来,我喜欢八大山人简洁、凝炼的水墨画。八大的画师法董其昌,其笔致简洁,有静穆之趣,且枯索冷寂,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气势,凸显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。此次展出的《山水花鸟册》中,画上只有一只毛茸茸的雏鸡,而静观其中,仿佛看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崽,唯有冷眼旁观的这只,孤傲、独立又不和。如此简单的画面,却有欲说还休的丰满。而一双脚站着的两只鹌鹑,以白眼向人的眼光,或俯首或仰头,羁骜不驯中有股忍辱负重的不甘,真是哭哭笑笑中,画尽人世的苍凉和悲欢。
“丹青不知老将至,富贵于我如浮云。”正是董其昌那样的列代名家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执念,才留下如此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,为后人学习和传承,并发扬光大。
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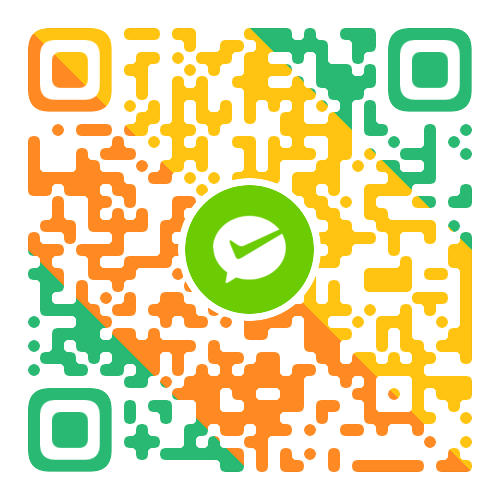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